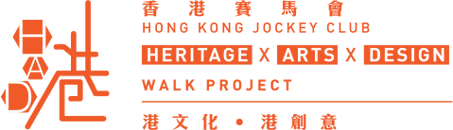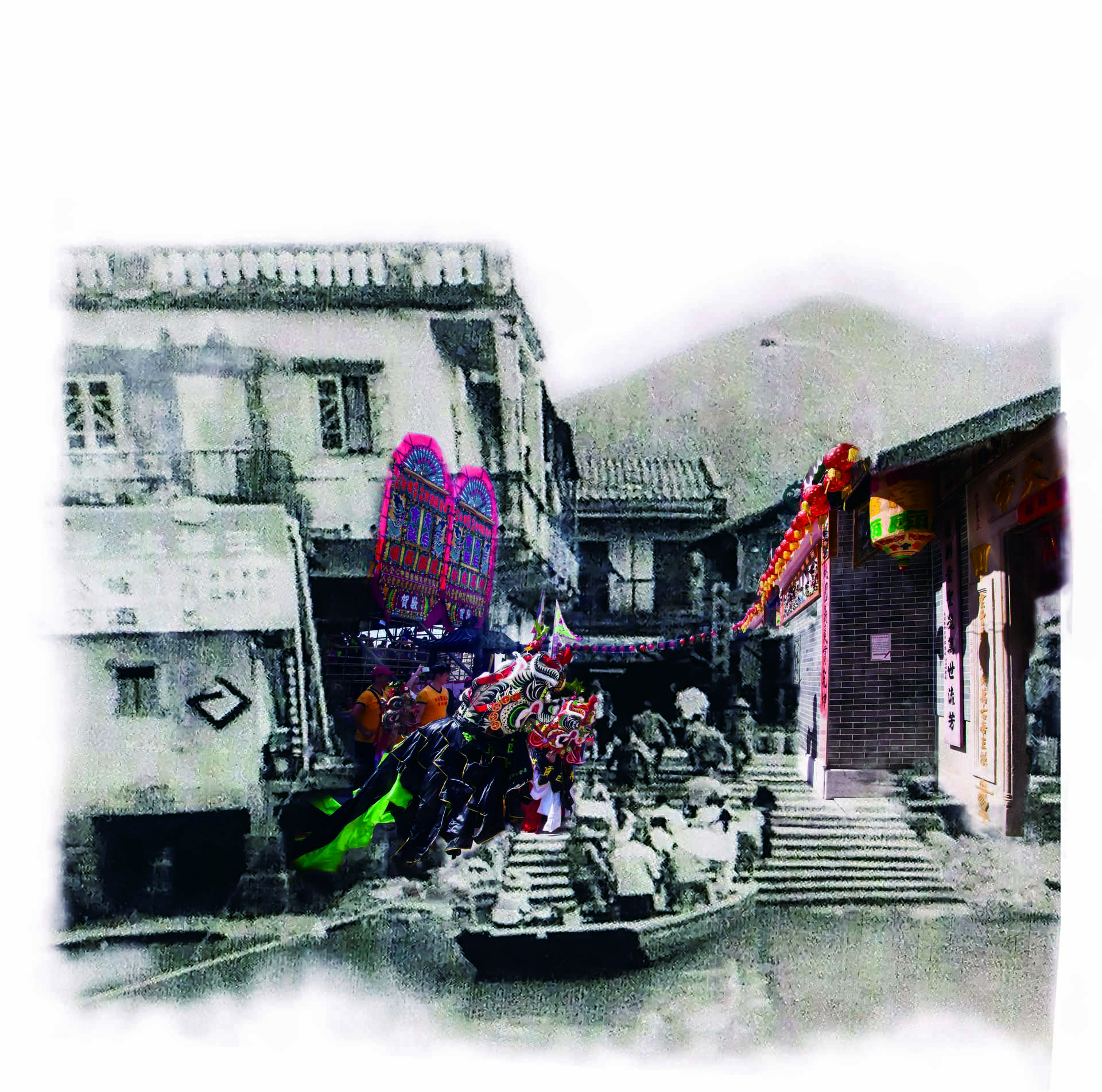文字|李英儀
圖片|文化葫蘆
拋得開時風仔懶
拋得埋時
撞斷嗰條三茄黃麻花包纜
起東風由獨牛身上過
過去獨牛又好行舟
大浪澳 小浪澳
咁多金銀浪來淘
三洲洲
三洲山上有棵紅粉藕
飯甑洲有個官門口
冇風駛船流過破邊洲《大星與小星》(節錄)
岸上人唱山歌,水上人嘆漁歌。
這一闋出自西貢。由獨牛洲、大浪灣至官門(今萬宜水庫),破邊洲入糧船灣,再至布袋澳、東龍洲、果洲、香港島。邊行邊嘆,灣頭角尾,潮汐高低,每多預告。
是討海業者世代相傳的叮嚀。
八十六歲的張明合,已許久沒嘆起行船歌了。白髮蒼顏的他,緊閉雙眼,竭力回憶,「我艘船拋到海中心,校兩盞大光燈照魚,坐喺度冇咩嘢,就整支歌。」實在是被困夜海。
漆黑海際,燈照引魚,良久,魚群趨光而至,方圍起罟網,打撈魚穫。歸程時船身負重,揚帆吃力,長夜漫漫,大海滄茫。原來歌謠不獨解悶,也壯士氣。
鬼門關
討海生涯,愈說愈駭人,「過咗個灣角,俾鯊魚咬死一個呀。」
有誰不驚慌?但餬口更迫切,張明合跟妻子,只好硬著頭皮。
以前捕魚多為家庭作業,夫婦出海,孩子隨行。張家有八子女,大仔張溢良八、九歲幫忙捕魚捉蟹,十二、三歲遇險,猶有餘悸。當日天氣惡劣,風浪很大,舉家往大陸平海至汕尾一帶捉龍蝦,「點解咁大風浪都出海?因為風平浪靜時,龍蝦唔會出嚟㗎!」突然一個大浪捲來,把漁艇弄翻。他們在海洋闖蕩,深知水性,「跌落海唔可以游向岸邊,事關再有大浪捲來,一定俾佢捲走。我哋於是游去另一艘船。」終於脫險。
浮家泛宅
那是五十年代,未有機動船,行船靠揚帆搖櫓;判斷靠天色風向水流。阿爸掌舵,阿媽做粗活,孩子看在眼裏,領悟謀生不易。
「我阿媽好叻平衡㗎!彎低身起網,背脊仲要孭住個細。」媽媽早兩年過身,排第五的張漢平惦起從前,「返到灣頭,阿媽煮飯,喺艇度食飯最搞笑,要夾實啲餸,唔好瀡咗去。」那年代漁民全居水上,歸航、停靠一處平靜海灣,一艘三十呎長罟仔艇,頓成家宅。灣泊所在儘量不變,摸熟環境,便可留在內灣作業,耐久都生起歸屬感。
張明合現居牆上貼滿舊照片,最大那張是風景海報,蜿蜒水道,小島環抱,逢有訪客他即介紹,「呢度咪官門灣囉,對落有個絞流角。晚晚七、八條船泊喺度。」就是他們多年棲息之所。
沒海履地
官門海峽於1969年給改建萬宜水庫,此前並沒堤壩,可直通太平洋,航道繁忙,魚穫豐富。「潛水捉到十隻八隻海膽鮑魚呀。」按水佬話,官門、乾門發音相近,事實官門真有乾的時刻,「潮退嗰時人都行到。」看來水上人很早在此落腳起名,一直賴這兒為生。
是以,當年政府說要填塞水道,他們很惶恐,再說水上人因沒地沒契,沒得賠償,張明合當即拉大隊上岸坐車出九龍,找上理民府,「嗰個總主任話你哋啲漁民仔有咩資格賠,我同佢講你哋讀飽書,唔好仔仔聲,我哋太公已經喺度攞魚,唔係無端端摸上嚟,你睇吓查吓係咪應該賠,唔好詐詐諦。」結果三十戶漁民遷上西貢對面海官門漁村。事隔多年,除了緬懷所失,還慶幸當時爭氣,沒給欺負。
蜑民文化
「我哋水上人成日俾人蝦㗎!」說此話者,是九十一歲的馬進興。他有親身經歷。
「以前喺西貢街我哋唔上得岸㗎!啲街上人一見到你就開口鬧,你啲蜑家仔走上嚟做乜呀?見你著鞋又唔俾你著,又出手打。」原來在四、五十年代,水上漁民仍被譏為蜑民、蜑蠻,指他們長期舟居,見識淺陋未開化。
馬進興當年在較偏遠的大鏟仔過活。那是橋咀島以北一小塊陸地,乃西貢最細的島,「得幾個洲仔連埋一齊。」地小,無人居住,石灘上則有幾個泥搭的漁寮,他和其他十來戶,日間泊好漁艇,爬上石灘曬魚、補漁網、曬漁網;晚上各自出海,睡覺繼續在艇上。他的艇十五、六呎,比張明合那一艘更小,但當時一家七口都住了進去。
手織籠
馬進興想多賺點錢改善生活,試過自製魚炮,第二仔馬義實也懂,「攞啲爆石原料,撈拜神香嗰啲粉落去,打落海可以炸暈成群魚。」但畢竟風險大,他其後放棄,倒是妻子張家妹親手織漁籠浸魚,至今仍留幾個在家,「呢啲鐵線籠係後期喇,初頭我用竹篾,一織幾十個,十個一排,放三排落海,籠入面安麵包皮,引啲魚游入去,有時塞到爆晒。」她笑嘻嘻道。
馬家六十年代隨教會遷上對面海聖伯多祿村,比張家還要早上岸。兩家孩子現都脫離了漁業,有的去開街渡、遊艇,有的做生意。
只是今時今日在西貢海,仍有人以捕魚為生。
網網千斤
他叫李馬來,鶴佬人,五十一歲。黑皮膚,高大壯實,手指頭比常人粗逾倍,做事很使勁,「而家西貢內海每晚有三組艇,我叔公、我阿叔同埋我。我哋喺西貢係四代漁民。」
黃昏五時他便開工,由海傍街魚市場,依次將五隻舢舨開出海,各載一部發電機,連接六盞燈照亮海面。然後他先小休,至凌晨一點,魚群已結聚,再駕駛罟仔艇逐隻舢舨靠近,圍網收魚,一隻舢舨作業半句鐘,分類魚穫另花兩個鐘,天光返抵魚市場。
近年因同業銳減,加上拖網絕跡,生態復甦,他魚穫大增,池魚、橫澤、絲鱲、烏頭,動輒千斤。對比上一代,連夜困在大海換一船魚穫,屬天壤之別。
那種苦頭他亦嘗過,當時年僅十二,「嗰時用汽燈,我晚晚瞓喺舢舨,瞓半個鐘醒一醒逐盞燈打氣。落雨照頭淋,最多搵張帆布冚吓,成個身都係濕。」
長大後他也耐得住辛苦,「我可以三日三夜唔瞓不停捉魚!要爭吖嘛,漁船多,要鬥快趕去魚市場,即刻賣,賣咗即刻返出海再捉。」只是沒多久,漁民已四散。
過盡千帆
海洋變化、經濟變化,八十年代幾乎所有西貢漁民都轉行。李馬來打地盤工。一位名叫鄭長娣的行家,轉營魚排。幾年過後,李馬來念念不忘,重操故業,魚排尚在。
現時李馬來除了交魚到魚市場,也賣鮮魚糧給鄭長娣。魚排位處大頭洲,一千平方呎,養六、七百擔龍躉、青斑等海鮮,再轉予市場。「好多魚排轉咗做遊客生意,但我仲係認真養魚。」他曾赴日本、台灣觀摩,羨慕彼邦養魚業有所屬政府支持,「唔似得香港,魚排泊隻船仔都話違規。香港就快連養魚都做唔到喇,要靠晒進口魚。」魚排本為漁民的退路,七、八十年代魚穫漸不成生計,才轉而養魚。不料幾十年後再遇留難,被迫二度轉型,餘下一些老業者始終不捨這片海,偶然去捉些魚,自用或供給遊客,維持運作,搭間小屋,住也賴在魚排。管不了是否違規。
根據政府統計數字,1955年西貢有漁船263艘、漁民1,904名。西貢區漁民聯會主席鄭景文稱,五十年代全西貢漁民估計上萬,至今大部分已散落陸上。
其實他們是很易辨認的。
某朝天曚光,在海傍街魚市場,艇未到,有位婆婆已在靜候。艇來了,一籮魚落地,婆婆趨前打量,也沒吭聲,李馬來鑒貌辨色,挑幾條給她。
至日上三竿,就見一地鹽醃烏頭沐浴在陽光下。